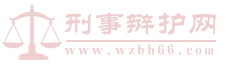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上诉人邹向安委托,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指派,本人做为上诉人的辩护人,依法出庭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上诉人与高云丰、王远征等人系委托关系,而非共谋诈骗的同案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一万步说,上诉人即使构成诈骗罪,所得款额也只有30万元,远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10万元,在上诉人家属已于庭前将30万元款项代为偿还的情况下,对上诉人仍课以十三年重刑,量刑畸重。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伙同赵刚、王远征、高云丰等人共谋诈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共计从王远征、高云丰、赵刚处收取210万元款项,均来自于被害人刘波:其中10万元款项,是王远征经手的(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案卷》(法律手续、口供卷)——邹向安诈骗案,2014年11月9日对王远征讯问笔录第4页9行),该款项来自于以求巩局长办事名义索要的30万元中后又由巩局长退回的20万元(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案卷》(法律手续、口供卷)——邹向安诈骗案,2014年11月9日对王远征讯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5行、第4页9行)。上诉人收到该10万元款项,高云丰、王远征、赵刚均知情。
另外200万元款项,经手人是高云丰,该款项来自程光荣、赵刚向刘波索要的400万元款项,程光荣收到400万元后转给了赵刚(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案卷》(法律手续、口供卷)——程光荣诈骗案,2014年11月8日对程光荣的讯问笔录第19、20页),赵刚将300万元又打给了王远征(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案卷》(法律手续、口供卷)——邹向安诈骗案,2014年11月9日对赵刚的讯问笔录第4页倒数第8行),王远征将其中200万元打给了高云丰(见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案卷》(法律手续、口供卷)——邹向安诈骗案,2014年11月9日对赵刚的讯问笔录第5页第5行),最后高云丰将200万元打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收到的200万元款项,高云丰、王远征、赵刚均知情。上诉人在事情不成的情况下,后来退回180万元给高云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通常认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犯罪行为两个必要条件。共同的犯罪故意主要是指各行为人必须存在关于共同实施特定犯罪行为的犯意联络。共同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各行为人在犯意联络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有无犯意联络是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前提,欠缺犯意联络则无共同犯罪故意,进而不构成共同犯罪。
程光荣、赵刚向被害人刘波索要400万元,虽因上诉人索要300万元办事费用而起,但不能说上诉人与程光荣、赵刚、高云丰、王远征等人(包括程光荣)形成共同诈骗的犯意联络:
第一,上诉人不具备与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等人(包括程光荣)形成犯意联络的条件;
被害人刘波请托程光荣办事,程光荣处于整个办事链条的最上一层级,他与被害人保持单线联系,程光荣向下找到赵刚,赵刚找到王远征,最后,王远征通过高云丰又找到上诉人,上诉人在本案中处于办事链条的最下一层级。从200万打款流程也可以看到,上诉人与高云丰、王远征、赵刚保持的是单线联系,上诉人从未接触过程光荣,也未见过被害人刘波,他只认识高云丰,与王远征、赵刚也只是初次见面,上诉人不具备与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等人形成犯意联络的条件。
第二,一审法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等人形成共同诈骗的犯意联络;
如果上诉人与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等人具有共同实施诈骗犯罪故意,必然在如何实施诈骗、如何达到诈骗目的、如何分赃等方面,达成犯意联络,但从以上三位与上诉人有过接触人的讯问笔录中根本无法看到这方面的证据。高云丰、王远征、赵刚与上诉人间约定事成收款、事不成退款,这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与诈骗不能等同,上诉人后来退回180万元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程光荣、赵刚等人的诈骗行为与上诉人无关。
上诉人索要300万元(实际收到200万元),而程光荣、赵刚利用与被害人单线联系故意多索要100万元,只能说明程光荣、赵刚有诈骗被害人钱财的故意,与上诉人无关。程光荣和赵刚等人就支付给上诉人之外的余款200万元、上诉人归还的180万元挪作他用,涉及的诈骗行为也均与上诉人无关。
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邹向安伙同赵刚、王远征、高云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一审判决上诉人诈骗他人钱财310万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作出两方面事实认定,做为上诉人符合诈骗罪特征的理由:其一,“邹向安自己没有能力办理刘波请托事项,其所称联系陶某等人办理此事,亦被对方明确答复无法办理,在此情况下,邹向安在前往青岛的短短几天内便将被害人刘波通过程光荣、王远征等人支付的10万元挥霍一空”;其二,上诉人“继续承诺通过其他人员办理,并向王远征、高云丰等人索要300万元(实际收取200万元,另外100万元约定事成后收取)的办事费用”,“邹向安亦无法提供证明原军委领导帮其办理刘波一案的相关证据”,上诉人将其中20万元没有转入原军委领导帐户,而是转入亲属和朋友帐户,“在无法办理所托事项后,邹向安未将钱款退给刘波,仅将部分钱款(部分钱款实为绝大部分钱款)退还王远征、高云丰,致使刘波进一步遭受损失”。
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得出结论:“邹向安主观上对被害人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法律规定,应对其参与实施的310万元诈骗数额承担责任”,以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一方面认可了上诉人接受请托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又认定上诉人自己没有能力帮别人办事,请托其他人又办不成,进而结合上诉人有部分款项没有退还的事实认定上诉人诈骗罪成立,该认定过程逻辑不通,没有任何说服力。
(一)上诉人与对方间系委托关系;
上诉人收取210万元钱款,接受请托为他人办事,并约定在事成之后再收取100万元款项,上诉人与请托人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如果事情办成,210万元不予退还做为报酬,请托人额外还需支付100万元;如果事情办不成,上诉人退回全部款项,这与“不劳而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罪显然不能等同。同案被告人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的口供,上诉人供述以及所打欠条均可以证明这种委托关系存在,一审法院也认可上诉人与对方之间是“请托”关系(与“委托关系”同义)。
做为委托关系,受托人可以亲自办理请托事项,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请托其他人办理;请托事项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请托的事项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完成请托事项获取的报酬可能得到法律支持,也可能得不到法律支持,这些均不影响委托关系性质的改变。
(二)上诉人是否有能力办理刘波请托事项与认定诈骗罪无关;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能力办理刘波请托事项,无非想说明双方委托关系成立之初上诉人就有“诈骗”故意。暂且不论上诉人没有能力办理刘波请托事项的说法是否成立、是否科学,本案中,上诉人接受请托的事项是通过人脉为刘波“冤案”平反,能否办成风险巨大,因此双方约定“风险”收费方式:事成支付全部310万元款项;事不成,退回已收取的210万元款项,既然如此,再去考证上诉人是否有能力办理请托事项已经失去意义。无论上诉人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初是否吹嘘自己的办事能力、是否默认别人对自己的吹捧,只要上诉人没有以为他人办事名义,行诈骗他人钱财事实,就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三)上诉人的请托人是否帮其办理刘波请托事项,也不能做为认定上诉人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之一。
做为委托关系,受托人可以亲自办理请托事项,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请托其他人办理,请托的事项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一审法院考证山东陶某有无明确答复无法办理、原军委某领导有无帮上诉人办理刘波案件,于本案诈骗罪认定没有任何关联,更何况证明犯罪是控方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原军委某领导帮其办理刘波一案的相关证据,本身即违反法律规定。
(四)一审法院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假借为被害人办事名义诈骗钱财;
前面已经阐述,上诉人与请托人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这与“不劳而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罪不能等同。上诉人在事情没有办成后立即返还210万元中的180万元款项,更是可以证明其没有诈骗对方钱财目的,如果其假借为被害人办事名义诈骗对方钱财,上诉人大可卷走210万元款项一走了之。
至于上诉人没有将全部210万元款项退还,而是截留其中30万元,虽然上诉人对此有所隐瞒,但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上诉人认为其应得的报酬。纵使将上诉人截留行为定性为临时起意的诈骗行为,也仅仅是区区30万元,而不能任意扩大为210万元,甚至310万元。
三、抛开本案定性之争,一审法院置诸多对上诉人有利的情节于不顾,对上诉人课以13年有期徒刑,量刑畸重。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诈骗310万元款项由三部分构成:上诉人退回的180万元、上诉人截留的30万元、上诉人预期收益100万元。
(一)关于上诉人退回180万元款项:
应该看到,上诉人主动退回180万元款项,既非良心发现,更非被动退回,而是兑现当初承诺,在事情未办成后第一时间主动归还,这不是委托关系是什么?这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罪能混为一谈吗?
纵使按照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构成诈骗罪,这部分主动退还的款项该如何认定:是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还是积极退赃?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做出其中任一认定,都对上诉人有利。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仅在判决中认定“邹向安的亲属代其退缴部分犯罪所得,依法对其酌予从轻处罚”,退缴30万元款项得以认定,但是180万元巨款并未涉及,舍大而取小,很难说一审判决做到了公平公正、量刑适当。
(二)关于上诉人截留30万元:
上诉人截留的是30万元,而不是210万元,更不是310万元,如何将全部310万元均认定为诈骗数额?
(三)关于上诉人预期利益100万元:
如果请托事情办成,除上诉人收到的210万元不予退还外,请托人额外还需支付100万元给上诉人,这部分数额显然并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竟将该部分款项计入诈骗罪数额之中。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无论事情是否办成、无论上诉人是否收到该100万元款项,上诉人只要动了这份“心思”,都将构成诈骗罪既遂,这难道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退一万步说,将该100万元纳入诈骗罪总数中,该如何看待上诉人索要这部分预期利益的行为:是犯意表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做出其中任一认定,都对上诉人有利,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并未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伙同高云丰、王远征、赵刚等人诈骗他人钱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纵使抛开本案定性之争,上诉人家属已代其偿还30万元款项加之上诉人更早归还的180万元款项,在上诉人已全部归还被害人21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仍课以十三年实刑,量刑畸重,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辩护人:杨洪波律师
年 月 日


 京公网安备 1101120200148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202001483号